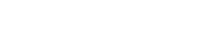我们为什么要撒谎( 二 )
许多撒谎者并非出于恶意而撒谎 , 只是对社会希求的一种降伏和称臣 。要知道 , 说真话一样可能是受不了压迫使然 , 可能是为了息事宁人 。从这个角度来看 , 真与假的界限是消弭的——皆因顺从而已 。
有趣的是 , 人们却偏对迈克的这类谎言痛打落水狗 。因为真正触了众人痛脚的与其说是被紫荆勋章欺骗之恨 , 不如说它刺激了自身的隐秘和不安:此类谎言是如此亲切 , 亲切到我们分不清是迈克说的还是我们说的 。正是这种对罪恶的亲切感 , 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。
其实 , 只要人们追求自己尽可能地符合社会标签 , 歹徒和圣徒的差别可能并不大 。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主教大人 , 没错 , 上帝之子一样会把匕首扎进情敌的心窝 。
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恐怕是:我们不自觉地在意标签 , 迎合标签 , 于是我们内化了标签 , 美化了标签 。那些生产着武士、妻子、女人、丈夫、作家、市长候选人的流水线 , 那些生产着你我他身上的社会“身份”的流水线 , 正是生产着谎言的流水线 , 更可悲的是 , 它甚至一并粉碎掉了真话的意义——只要人性被社会性压迫着 , 那真话与假话都等价于“自我”的消失 , 而我们也必将堕入软弱的无边漩涡 。
“自我之语”与“非我之语” , 或许是比“谎言与真话”更实在的二分法 。倘若不把人从标签之下解放出来 , “真”的可能性就永远是奢谈 。所以一切的前提都在于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 , 我们可能做出什么来 , 否则我们只是一群群穿着社会角色睡衣的梦游者 , 而在梦游状态下做出什么都不足为怪 。
我们因无法正视欲望而撒谎
再没有比个人电脑被警局搬走调查更不堪一击的事了 , 于是我们看到 , 两度娶妻生子的迈克的“犯罪动机”是一沓从他电脑里打印出来的男同色照 。然而这真能坐实迈克杀妻?还是仅仅揭开了迈克数十年的疮疤 , 让他像个在聚光灯下的可怜小丑?
一个和内心真实渴求搏斗到苦不堪言的人 , 必然会走向杀妻的一天——这才是人们相信的逻辑 。比如《罗生门》里的樵夫的谎言可以来自于更加廉价的欲望:仅仅想拿走一柄死者的短刀 , 就足够让他对目击的杀人现场撒谎了 。
无法正视自身欲望 , 不敢抚摸这只狮子鬃毛的人 , 最后只能献身于无穷无尽的谎言 。因为欲望的狮子是不会变成猫的 , 它必然对钻过人性这个火圈跃跃欲试 。
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最后迈克坐了86个月牢出狱后 , 终于鼓起勇气拒绝新女友的原因——他受够了对自己的性取向欲盖弥彰 , 不想再为软弱买单了 。
直至结尾 , 迈克到底是否杀妻也不得而知 , 但在妻子死去当晚 , 他看着她的侧影 , 对着游泳池自语的那几句却意味深长:“曾经有一刻 , 我知道自己是谁 , 然后事情接踵而至 , 让我离那刻越来越远 。”
没人能接受那挡在自己和“那一刻”之间的任何东西 , 这是确定无疑的 , 虽然《阶梯之间》所取材的真实案件也并没有确定的真相 。假如说杀妻是可怕的 , 那么我们无法确定迈克到底是否杀妻更是无法忍受的 , 但好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, 有压迫处即有软弱 , 有软弱处即有谎言 。
我们因为害怕失落而撒谎
于是《罗生门》以及它的一个个变体 , 包括《阶梯之间》无不在向我们展示:人人都是杀妻犯 , 人人也可以都不是——如果我们跳脱软弱与谎言的话 。
至于如何跳脱?
归根到底 , 谎言来自于害怕失落 , 只是如果连自我都已然失落了 , 那我们还在害怕失落掉的还能是什么?
过去心不可得 。我们却仿佛逆水行船 , 不断被冲刷回了过去 , 以至失掉了本就微茫的一点前途和芬芳 。即便如此 , 那将我们不断冲退到过往的水浪不是别的 , 正是我们自己 。
- 娱乐圈必打榜单,张绍刚为什么这么让人讨厌?
- 不忍心批评,却还是忍不住问些为什么
- 中年女演员不服老,非要演十几岁的少女
- 好人有好报?为什么在《人世间》里我看到的都是失望?
- 为什么向佐选择当哑巴新郎?
- 《星汉灿烂》6个重要配角都参加过选秀节目,其中5个是“快乐男
- 王冰冰和徐嘉余恋情官宣要从7月20日说起,两人恋情官宣
- 看了丁嘉丽以前的照片,终于知道孙红雷为什么和她在一起了
- 成龙回忆闯荡好莱坞经历:我不要美国市场
- 要不是节目组的“放水”,李晨这次也不会被骂上热搜